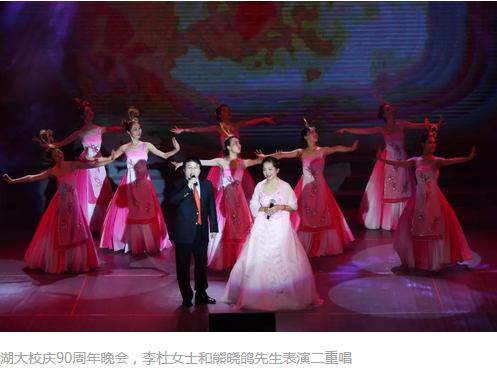又是一年高考季。一转眼,时光离我的高考远了40年,回顾我的高考往事,却觉得一切都历历在目。
1978年初,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,被录取到湖南大学化工系分析化学专业。虽是1978年入的学,但考试是在1977年进行的,所以还是被称为77级。能成为中国77级大学生的一员,是我这辈子引以为荣的一件幸事。
1977年的高考,真是千军万马同挤独木桥——11年没有高考了,570万人同时报考,录取了27万人,录取率不到5%。若再把大专和中专去掉,本科学校的录取率只有2%了,我能考上湖南大学真是有些“走狗屎运”的感觉。后来再和同学们回忆起当年高考的情形,发现自己比他们又要幸运很多,因为我有个强有力的老爸做后盾,我的高考可以说成是我和父亲的高考。
1977年,那时我已在乡下当了两年多的知青。对知青来说,最折磨人的并不是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困苦,而是你不知道等待着你的命运将是什么,好比在茫茫大海里奋力游着看不到彼岸,或有船只从你身边驶过,却不是来救你的。这时知青点已陆续有人参军或是招工走掉了,每离开一个人都会引起知青点焦虑情绪的蔓延。
我在羡慕之余,更是感到前途渺茫心灰意冷。部队或是工厂都不是我想去的地方,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新闻记者,即便实现不了,我也想读书深造,不管是什么专业,至少还可以当个技术员什么的吧?我不甘心一辈子从事简单劳动。
当时读大学的名额极少,并且是需要公社推荐。我一个普通知青,大学的大门就是开错了也不会朝着我啊!就这样,时不时地被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煎熬着,无以自拔。
1977年5月,正值我情绪极为低落之际,中共中央转发了还未复出的邓小平写给中央的一封信,政治上极为敏锐的父亲立即意识到中国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,便给我写了一封信,嘱咐我有空时复习下功课,可能会恢复高考了。寥寥半页纸,有如一声春雷,让我顿觉自己的人生总算是有了盼头,心想只要是通过考试来录取大学生,自己还是有些希望的。
文化革命那些年头,大家都没读什么书,相比之下我还算有幸学了点东西:
一是虽然家里对我的功课也是从来不过问,但父亲对我的写作阅读兴趣还是做过一些因势利导的培养,不知不觉中给我的语文打下了较厚的功底。
二是我高一那年正好遇上邓小平复位,大概有一年半左右的光景吧,这段时间学校对教学抓得特别紧,加之长郡中学是一所老牌名校,老师的教学水平可都是一级棒的,我也就心无旁骛地扎扎实实读了一年半的书。

三是我中学期间在班上有两个聪慧绝顶的闺蜜,她们俩学习成绩都特别拔尖,三个女孩整天腻在一起,本来懒惰的我,也不好意思被她们比下去,所以也一直不敢过于松懈,大家私下里暗暗较劲,你追我赶,以至于到了高中后我们一不小心成了年级的三位女学霸。
四是下农村后只搞了一年劳动,大队上的小学要办个初中部,见我文笔还不错,便挑了我去当初中教师,这样我便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,在学习时间和精力方面都要略占些优势。
此时我当老师快有一年功夫了,同时兼任着初中的数学、英语及政治课程,还有小学六年级的语文、音乐课,下学期还要增开物理、化学。
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荒唐,区区一高中生,本就没读什么书,同时还兼这么多门课,不误人子弟才怪呢!所以一直暗暗佩服从农村学校毕业考上来的同学,心知靠我等这样的山寨老师那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,得全凭着他们自己的天赋和努力。这是题外话。
繁重的教学任务让我忙得不可开交,尽管有了奋斗的目标,可惜自己是个很不能吃苦的人,那什么头悬梁锥刺股的励志故事对我是没什么效果的,工作之余已没什么精力顾及复习功课了,只在偶有空时翻下当时的高中数学教材,那也是做做样子,每天等备完课改完作业,眼皮早打架了,那教材简直就成了我的床头催眠书。
此刻心想,父亲也不过是猜测罢了,哪一天恢复高考还难说呢!所以也就不怎么着急,复习的进度很慢,质量如何更是不得而知。
没想到形势发展如此之快,这年秋天国家就宣布了12月份恢复高考的决定,此时离考试已时日不多了。我们这些知青就在乡下报名,分文科和理科报考。我打算报考文科,想圆了这当新闻记者的梦。
可父亲此时却一反鼓励我爱好文学的常态,又是电话又是口信的,坚决地阻止我报考文科去当什么新闻记者,见我不置可否,硬是把我叫了回去,苦口婆心地做我的工作。他说学文的政治风险太大了,说不定哪天就会惹祸上身。
大哥说得更是决绝:“报什么文科,你想当右派啊!你报文科我就和你脱离关系!”委屈的我眼泪汪汪。不过最后善于攻心的爸爸用一个理由说服了我:“你不是不喜欢当老师吗?学文科当老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,除非你考得上北大,要不就到了师范学院了。”

才20岁就担任了N多门课程教学的我,不检讨自己的课教得不好,却埋怨学生太笨,总觉得自己一天到晚都在对牛弹琴,真是厌烦透了教师这个职业,一听说读了大学还得去当老师,便立马投降了,同意报考理科。
此一决定,可伤了我的语文老师萧老师的心了。萧老师是解放前湖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,已到了退休的边边上,事业心却还是很强。她一直很器重我,也很关心我的报考。当得知我报考理科的决定时顿足道:“你怎么就考不上北大?考得上的!”可我哪有考上北大的雄心壮志和信心?我的第一目标是跳出农门,这可是个生死赌注随意不得!
她见我不松口只好无奈地叹道:“我年轻时就想当个作家没当成,这辈子就一直想培养个作家出来,教了这么多年书只遇见了两个有文学天赋的学生,你是一个。结果那一位学了美术,你又报了理科,我的理想算是完了!”我听了也很难过,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毁灭萧老师理想的罪魁祸首,只好默默无语,诺诺地离去。
其实当时我也真是无知,根本不知道除了北大和湖南师范学院,还有很多其他的学校设有文科专业,就这么轻易地被老爸唬住了,从此断了当新闻记者的梦想。人得认命,我费尽心机不想当老师,几经辗转后却还是当了老师,最后虽仍然不喜欢这个职业,但也没那么厌恶了,这也是题外话。
从现在才开始正式的复习。爸爸检查了一下我的复习状况,不禁大惊失色,说这样下去不行,只有一两个月了,你得想办法请假,回来我带你复习。于是三哥托他一位朋友带我到医院去找熟人开病假条。因从未说过谎,到了医生跟前我竟一句话都不敢讲,全是那位哥哥帮我在说,好在很顺利地拿到了一个月的病假条。
一个月以后假满了,我不好意思再找熟人了,便莽莽撞撞地直接跑到大队书记那儿请假,说我病还没好。老书记竟一点都没有怀疑,还顺着我的话说:“那是没好,看你脸色那么苍白,回去再休息一下吧!”学校的校长也没有为难我半句,继续放我回了家。
比起很多不敢耽误出工、只能在工余时间复习的知青来说,我是幸运多了,多了好多温习的时间。后来想想,医生、书记、校长,他们哪会看不出我这拙劣的谎言?其实都是在暗暗地帮我。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,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惜为难自己帮助了我。
一直到快考试了,我才回到农村,也不知道我的那些七七八八的课是谁给接下来的,直到N年后我自己担任了主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,才意识到当时我给学校带来了多大的困扰,可我却从来没有当面感谢过他们一句!

在当时的中国,家里有个当知青的孩子,那就是每一对父母最大的心病,能考上大学自然是最好的出路,关键是还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,只是竞争如此之激烈,不得不背水一战了,就和现在所有的考生家庭一样,全家人把我的高考当成了头等大事,成败在此一举。
大概是知道我们家有一位高考生吧,往日里络绎不绝来找父亲的客人也一时绝了迹。父亲直接担任了我各门功课的辅导老师。母亲则承担了全部的家务。那时家里房子很挤,总共才两间很小的房间,哥哥们全搬到单位上去住了,把一间房腾给了我。
房间里没有书桌,只有一张破旧不堪的折叠小饭桌,因房间小,平日里吃完饭是要把桌子收起来的,在我复习的那一个多月里,就没有再收起来过,吃过饭妈妈把碗筷收了擦一擦桌面,铺上一层报纸,我和爸爸一人坐一方便学习起来。
这一个月,是我人生中和父亲相处得最紧密的一段时光,父女在共同作战攻克我的高考堡垒,非常的温馨。
父亲否定了我曾看过的文革教材,他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套文革前的高中教材。因为时间太短,父亲说数学分数高,先保证把数学考好。他每章都会抽出些题目让我做,做得好的就让我过,做得不好的就跟我讲课。我记得他说我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学得不好,重新让我学了一遍,这恰巧是我高二第二学期的学习内容,那时邓小平已被赶下了台。可见我的学习基础居然是与邓大人的政治生涯息息相关的!
待到教材看完后,父亲每每下班后又不知从哪里找回来些题目让我做,这些题目比书上的要难一些。到考试时,我的数学基础打得很好了,拿起试卷一气呵成,应该是只粗心丢了两分。父亲只是一位中学校长而并非数学老师,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数学基础那么好,比教数学的妈妈还要好得多。
因时间实在是有限,我在物理和化学方面花的时间不多,父亲只是把最重要的内容勾选出来让我看,做做例题,有问题问他。到底是题做少了,投入和产出是成正比的,所以考得也一般。因妈妈是长郡中学的老师,我还有幸听过几次长郡中学组织的复习课。
我对其中一次化学复习课印象颇深,主讲是长沙市有名的刘佑文老师,人称刘化学,他的课不仅条理性很强,且风趣有味,那些难点从他嘴里出来都异常轻松。记得当时对氧化还原反应中的几个概念我总有些迷糊,刘老师说你们记住五个字就行了:“升失被氧还”,即化合价升—失电子—被氧化—还原剂。这个口诀我一下便记住了,而且记了一辈子,后来还传授给了高考中的儿子,哈哈!
在当时,除了还没离校的应届生外,我的这种学习条件应是得天独厚的了,有什么问题随时都有爸爸给解答,所以学得很轻松,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大多数知青都只能闷头看书或相互讨论,有问题上哪儿问去?所以,有个如此睿智如此爱我的老爸,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。

语文占着自己基础还行,根本没理过,其实感觉考得并不见得好。萧老师阅卷时到作文突出的试卷中去翻找,以为里面会有我的试卷,结果没有。政治更是不知从何复习起,只好听了一次复习课便没管过了,结果政治考得最烂。
那时不知为什么考试结果是保密的,只知道湖南省本科的录取分数是平均55分,公社主管文教的主任事后告诉我,我的平均分数是78分,还说我政治考得太差了,差成什么样子至今也不得而知。现在想想,父亲太有先见之明了,要真让我考文科,别说考北大了,只怕是师范学院都考不上呢!
虽说我考上重点大学,但说实话,有如此优越的学习条件只考了这个分数,我实在是有点对不住人。好在当时家里对我要求也不高,只要能跳出农门就心满意足了,呵呵!
最后,回过头来忆一忆我们家那张神奇的小饭桌。一张油漆斑驳的方桌面,和它底下的活动支架是不配套的,那四只脚也十分不稳,轻轻一碰就会挪地方。我们家人喜欢用它来温习功课,因为师生可以同桌,有时学生还不止我一人,邻居家孩子也跑过来蹭蹭课什么的,全围在这一张桌上。从这张小饭桌上,父亲先后培养了四位大学生。我是第一个,接着有我三哥考上了湖南师大,堂弟考上了清华,表妹考上了湘雅。
最神奇的是三哥,他是68届的初中毕业生,15岁就被迫下了农村。文化水平说是初中,实际上小学都没读完就遇上文化大革命,初中的大部分时间在挖防空洞。后来凭着自学的小提琴特长考到剧团拉琴。见我考上了大学,他也决心要报考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,爸爸测试了一下他的数学水平:1/2+1/3=2/5。
爸爸说只有半年了,凭你这基础理科是肯定考不上的,考文科吧!于是给他制定了一套专门的考试复习方案,三哥也是拼了,那劲头那才真叫头悬梁锥刺骨呢!78级居然考上了师大历史系,后来还读了研究生。在父亲的辅导下,数学虽说考得不好,但也没拖太多后腿。
送走了四个大学生后,爸爸整天得意地夸他那张宝贝小饭桌,来了贵客都在那张桌上请吃饭。大概小饭桌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吧,便不大尽职了。
有一天,爸爸特意蒸了碗泥鳅招待远方回来的叔叔,蒸好的泥鳅刚刚端上桌,“哗”的一声桌子突然垮了,泥鳅泼了一地。我们面面相觑,一时鸦雀无声,不知是可惜那碗泥鳅,还是心疼这张小饭桌。
于是,爸爸口口声声要当作传家宝带走的那张破桌子,终究没有随着我们搬入新家。